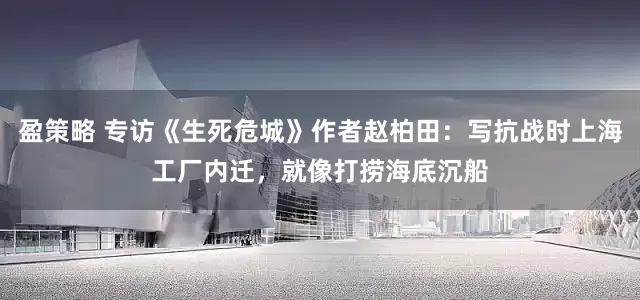
1937年9月的蘇州河上盈策略,張帆掛櫓的木船里藏著工廠拆卸的機(jī)器。這些運(yùn)速不高的船只,在獲國民政府的通行批文后,要一路上躲避日軍的追襲,才能先抵蘇州或鎮(zhèn)江,而后轉(zhuǎn)至武漢。
往前兩個月,“七七事變”后、“八一三”淞滬會戰(zhàn)前,緊張的態(tài)勢之下,為確保資源集中供給戰(zhàn)事和避免工廠被收直接資敵,上海的工業(yè)內(nèi)遷迫在眉睫。當(dāng)時,全國三成以上的已登記工廠都集中在這座遠(yuǎn)東第一大城市。
在淞滬會戰(zhàn)爆發(fā)前后的背景下,從7月到戰(zhàn)爭收場的11月,短短四個月時間,一場關(guān)乎中國經(jīng)濟(jì)命脈的工廠物資內(nèi)遷計劃如何展開?這是作家、華語文學(xué)傳媒大獎獲得者趙柏田最新長篇非虛構(gòu)作品《生死危城》要打撈的歷史記憶。該書最初刊載于《收獲》雜志,今年8月由浙江文藝出版社KEY-可以文化推出。

2025年8月,正值中國人民抗日戰(zhàn)爭暨世界反法西斯戰(zhàn)爭勝利80周年之際,浙江文藝出版社KEY-可以文化推出《生死危城》。浙江文藝出版社KEY-可以文化供圖
英國詩人柯勒律治說,憑著墻上的幾個點,可以掛起一幅心靈的掛毯。這給了趙柏田啟發(fā),持續(xù)多年寫作現(xiàn)代中國的他,在錨定鐵路、外交、金融業(yè)、晚清以降知識人的精神流變之后,將筆觸落到了現(xiàn)代中國的工業(yè)領(lǐng)域。
對于非虛構(gòu)寫作,趙柏田要求“每一滴露水都有其出處”,而同時身為小說家的他,又希望文本具備高度的可讀性。在《生死危城》里,他把主持內(nèi)遷的科級官員林繼庸作為故事眼,將目光掃過更高級別的官員、實業(yè)家、工廠主、工人,以緊張的敘事節(jié)奏呈現(xiàn)戰(zhàn)爭爆發(fā)前后的內(nèi)遷困境。
八十八年前,上海的實業(yè)家們或寄希望于內(nèi)遷,或以為租界可保無虞,或主張前往香港,不同想法影響著各自今后的命運(yùn)。最終,林繼庸主持工廠遷移期間,除協(xié)助搬遷國營的工廠外,上海的工廠共遷出了146家,機(jī)器和材料14600余噸,技術(shù)工人2500多名。趙柏田說,這些工廠和人,成了中國工業(yè)的火種。
趙柏田長居上海,在寫作這本書時,他常常會到老戰(zhàn)場遺址或者工廠舊址,盡可能地回到歷史的現(xiàn)場。上海老建筑還能找到舊時光的蛛絲馬跡,實業(yè)家的工廠換了一種方式活下去。
9月16日,在上海黃浦江畔的陸家嘴,南方+記者采訪了趙柏田,以下是對談內(nèi)容。
寫上海工業(yè)內(nèi)遷往事,就像打撈海底的沉船
南方+:“八一三”淞滬會戰(zhàn)十分慘烈盈策略,很多書籍也是直接寫戰(zhàn)爭。您為什么選擇從工業(yè)內(nèi)遷的角度寫?
趙柏田:這個角度不是刻意尋找的,它是自動浮現(xiàn)出來的。好故事不是編出來的,是你發(fā)現(xiàn)的,特別是歷史寫作。好故事像海底的沉船一樣,等待寫作者把它打撈上來。
過去幾年,我做現(xiàn)代性的研究和寫作,從外交、鐵路、商業(yè)和金融、知識分子的思想和精神流變?nèi)デ腥耄瑢懥瞬簧俟适隆5矣X得有一個很重要的板塊,就是中國的工業(yè)化仍然沒有觸及。工業(yè)文明帶來了現(xiàn)代性的曙光,如果沒有這一塊的話,那么我對整個中國現(xiàn)代性的呈現(xiàn)是不夠完整的。
幾年前,我寫中國現(xiàn)代金融業(yè),收集了很多上海實業(yè)家的材料。我發(fā)現(xiàn),民國時期上海大大小小的銀行對實業(yè)有很大支持。當(dāng)淞滬會戰(zhàn)爆發(fā),那些工廠背后的人就動了起來,命運(yùn)的齒輪也開始轉(zhuǎn)動。可以說,在寫完上海的銀行家和現(xiàn)代中國的金融業(yè)之后,實業(yè)這一領(lǐng)域的人和事也漸漸地鮮活了。

蘇州河碼頭上的木船。成千上萬噸的機(jī)器就是用這樣的木船運(yùn)到蘇州、鎮(zhèn)江,再換船,沿著長江運(yùn)入內(nèi)地的。受訪者供圖
這次遷廠改變了中國工業(yè)的格局, 1937年以前,中國內(nèi)地的工廠非常少,幾乎沒有現(xiàn)代工廠。不要小看遷出的146家工廠和2500個工人,他們有許多留在了內(nèi)地和西部,成了中國現(xiàn)代工業(yè)的火種。寫這本書,是為了讓今天的讀者看到,在民族危難之際,為了工業(yè)血脈的延續(xù),曾經(jīng)有這么一群中國人,作出了不屈努力。在書的扉頁,我引用了穆旦的一首詩《贊美》,就是為了謳歌這些內(nèi)遷者的不屈意志和頑強(qiáng)生命力。
書是在2023年12月完稿,《收獲》2024年2期發(fā)表,我當(dāng)時在《收獲》約寫的創(chuàng)作談里說,它是我寫現(xiàn)代中國的最后一塊拼圖。不過,之后我又發(fā)現(xiàn),現(xiàn)代中國其實還有一塊更大的“拼圖”可能要去書寫,那就是科學(xué)。從洋務(wù)運(yùn)動到民初,科學(xué)的概念和內(nèi)涵發(fā)生了一個很大的變化,從最早的器物引入,發(fā)展到之后求真求知的理念的形成。
南方+:這本書的寫作跟您自身的經(jīng)歷經(jīng)驗有關(guān)系嗎?和書里很多實業(yè)家一樣,您是寧波人,跋里也提到您曾祖輩里有人曾經(jīng)是工廠主。
趙柏田:作家選擇的題材、所寫的故事,跟他的生活環(huán)境和經(jīng)歷有很大關(guān)系。寫作者進(jìn)入文學(xué)世界的道路,永遠(yuǎn)是離他最近的一條。所以我的早期小說寫南方鄉(xiāng)村,喜用兒童視角。隨著寫作履歷的增長,寫作題材和風(fēng)格更加脫離不了經(jīng)驗的影響。
我老家浙江余姚,是王陽明出生的地方,我生活了很長時間的寧波,又是很早就開放的五口通商口岸城市之一,文風(fēng)和商風(fēng)都很盛。這些人和事會自然進(jìn)入到你的生活場域,成為你的生命和文學(xué)記憶。
因此,關(guān)于歷史的一切,王陽明、浙東學(xué)派、新文化、現(xiàn)代性主題下的中國往事等等盈策略,可能是我潛意識里本來就有的東西。我寫《生死危城》時,曾數(shù)次想起家族里一位前輩的故事,他原來也是一個實業(yè)家,也是一個小工廠主。
回到歷史現(xiàn)場:集一手資料,到遺跡現(xiàn)場
南方+:在寫作過程中,您如何確保材料的嚴(yán)謹(jǐn)性和敘述的流暢性,使文本可讀性高且不失真?
趙柏田:非虛構(gòu)寫作已經(jīng)到了建立自身美學(xué)規(guī)范的時候。非虛構(gòu)的寫作倫理就是求真,大大小小的事件,包括人物的對話,都要有出處和依據(jù),就好像每一滴露水都要有其來歷。這本書引用了大師檔案、報告、當(dāng)事人的口述史、電文,出書后只有選擇地在文下加了一些引用來源。加注,表明的是我的一種寫作態(tài)度,那就是對你寫下的每個字負(fù)責(zé),對歷史負(fù)責(zé)。
至于材料的選取,我主張要盡可能回到歷史的現(xiàn)場。回到歷史現(xiàn)場有兩種方法:第一種是親身到現(xiàn)場,去觀察地形地貌。但半個多世紀(jì)過去了,老戰(zhàn)場的遺址或者工廠舊址已經(jīng)物是人非。如果你滿腔熱忱去找,希望能發(fā)現(xiàn)跟記載或者圖片對上號的東西,可能真沒有了。所以,更重要的,是去感受、捕捉歷史的氣息。
更重要的一個途徑,是去尋找與當(dāng)事人相關(guān)的第一手資料。比如日記、書信、電文、檔案、口述實錄,還有回憶錄和后來學(xué)者的研究。中國傳統(tǒng)文人的習(xí)慣是用寫日志來記錄和反省自己的言行,留下了大量日記。回憶錄由于已經(jīng)隔了一段時間,可能有對事件的美化或者記憶的偏差。
寫作上,我是一個慢人,一步一步來。我會用比較長的時間去感受、去規(guī)劃、去收集。在收集和研究的階段,我會為筆下的題材、故事、人物建立一個資料館或者小型圖書館。回到《生死危城》這本書,關(guān)于這次遷廠的歷史,我搜集閱讀了上百本資料。
寫書還是要讓讀者看得進(jìn)去。有時候,我說我不是一個作家,我是一個敘事家,一個寫作家,研究用什么樣的敘事,來貼合筆下的人物和故事。
南方+:我對書里的一個細(xì)節(jié)印象深刻——因為炮火炸斷了電話線,張治中將軍從南翔指揮所驅(qū)車到江灣鎮(zhèn)了解情況,后面為避開日軍轟炸,他下車步行。途中遇到一個騎自行車的傳令兵,士兵問他,“怎么回事,現(xiàn)在司令也只能乘11號車(指步行)了?”這個細(xì)節(jié)很生動,更重要的是,它不符合長幼尊卑的傳統(tǒng)觀念,我們應(yīng)該如何理解?

工廠林立的閘北區(qū)在劇烈的爆炸聲中升起了濃煙。受訪者供圖
趙柏田:我在張治中的戰(zhàn)場記事里發(fā)現(xiàn)了這句對話。一個士兵說出這樣的話,也能反映出當(dāng)時戰(zhàn)場的形勢已經(jīng)有點亂了。他言語里面既有一種無奈,也有對長官的調(diào)侃和反諷。如果整裝待發(fā)、士氣高昂,一個士兵不太可能說出這樣的話來。透過這種無奈,我們會發(fā)現(xiàn),在這場血與火的戰(zhàn)場的絞殺里,無論是將軍還是士兵,每個生命都是脆弱的。另一方面,從文本上來說,像這樣的一句不經(jīng)意的話,會帶給全書生動的氣韻。
人,終究抵擋不過時代所造的勢
南方+:您寫這本書有沒有遇到什么瓶頸期?對主線人物和群像人物的選擇有什么特別考量嗎?
趙柏田:主要是一手史料太欠缺。我在上海檔案館和圖書館找了一些關(guān)于工廠內(nèi)遷的材料,但所獲不多。后來,我找到了著名歷史學(xué)家張朋園主持的口述史《林繼庸先生訪問紀(jì)錄》,在此之前,內(nèi)地有關(guān)林繼庸的記載幾乎沒有。林繼庸是立起這本書的脊椎骨,在上海民族企業(yè)內(nèi)遷方面,他是一個靈魂性的人物。如果沒有林繼庸這個第一當(dāng)事人的訪問紀(jì)錄,這本書是沒法寫的。這本訪問紀(jì)錄讀起來很枯燥,但它實打?qū)嵉卣f、有一說一,符合我對歷史的求真態(tài)度。

主持上海工廠內(nèi)遷工作的林繼庸,是資委會的一個科級官員。他是廣東香山縣人。受訪者供圖
戰(zhàn)爭爆發(fā)了,生活在這座城市里邊,無論你是大企業(yè)主、小工廠主,還是工人,命運(yùn)都改變了,每個人都要有自己的方式去應(yīng)對。基于這樣的考量,寫人物的時候,我選擇了不同身份、不同結(jié)局的群像式人物,既有無錫榮氏兄弟、寧波幫的鋼鐵大王余銘玉,也有商務(wù)印書館當(dāng)家人王云五,小工廠主沈鴻,還有寄希望于租界的嚴(yán)裕棠。
南方+:您在跋里寫“人,終究抵擋不過時代所造的勢”,這句話應(yīng)該怎么理解?會不會太過宿命論?您會用歷史的眼光打量當(dāng)下嗎?
趙柏田:人是被時代塑造的,成與敗,都由時代塑造,這個是歷史的經(jīng)驗。這不是宿命論,這是歷史和命運(yùn)的一個事實。
我不會用歷史的眼光去打量現(xiàn)在。對于藝術(shù)家來說,歷史可以成為審美的對象。作為歷史寫作者和研究者,歷史是認(rèn)知和求真的對象。歷史所包含的教訓(xùn)與經(jīng)驗非常深刻,但我們很難把這些教訓(xùn)和經(jīng)驗移用到當(dāng)下,這樣做無異于把歷史工具化、功利化。我覺得歷史應(yīng)該培養(yǎng)的是更加通達(dá)的人生態(tài)度,更加智慧的審視目光,以及更加開闊的胸懷。
南方+記者 張晉 朱紅鮮盈策略
可盈配資提示:文章來自網(wǎng)絡(luò),不代表本站觀點。


